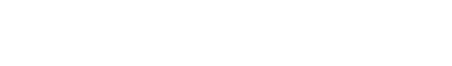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最新动态
我中心费晟副教授就澳涉华智库接受《环球时报》采访
发布日期:2017-05-24
2017年5月23日,我中心费晟副教授就澳大利亚涉华智库接受《环球时报》采访:
针对被认为“客观中立”的“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费博士表示该智库所在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是拿联邦政府预算运营的,所以其下属的中国研究机构也可以算作政府智库。因为澳政府讲究实用主义,诸如中华全球研究中心这样有政府背景的智库一般不会走极端,不会特别远离中国,也不会特别亲中。中华全球研究中心“务实”的特点,从它邀请休·怀特及其所持观点便可窥一二。
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是澳大利亚为数不多的专门针对中国的研究机构。相比欧美国家,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起步较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澳汉学家费子智的数本著作出版,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成果开始引起世界关注,但整体中国研究还具有一定局限性。转折点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开始偏向亚洲,在此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于1989年在墨尔本大学宣告成立,对中国的研究在澳大利亚逐渐推广开来。
提及澳大利亚存在“反华”的中国智库一说,费博士表示,很难将一个智库用“反华”或者“亲华”来归类。澳大利亚智库中的人员立场分化常常很大,即使在一个智库中,有些学者倾向于对中国持温和态度,有些比较激进,这其实和他们的学科背景和关注点有关。
而对于“一般真正处理过澳大利亚外交事务、在一线有工作经验、受过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训练,以及推动中澳建交和‘脱欧入亚’战略的学者,相对来说会对中国有全面、客观的认识,比如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任格瑞,以及澳中关系研究院的鲍勃·卡尔。”费晟解释说。任格瑞有26年的外交经验,两度在北京任职,当过澳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而另外有一批学者是国际政治专业训练出身,研究国际或地区战略和安全问题。费晟表示,他们基本上完全受美国国际政治训练影响,缺乏对中国历史和内部问题系统的关注,只是出于特定国际政治理论的分析习惯、或者只把中国作为澳大利亚外交的一个当前客体认识的。“这些人对中国的态度和印象容易比较刻板,无论如何要维护澳美关系,对中国所有的积极活动都容易理解为威胁或者挑衅等负面信息。他们对中国本身了解不多,把中国放置到一个他们接受的结构中去研究,很容易把中国往消极方面去理解。”
费博士同时强调,这并不绝对,比如澳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主任布兰登·泰勒是研究地区安全和战略问题出身,但他对中国就十分友善。此外,有一些中国研究学者的配偶是华人,因此他们至少在文化上对中国不那么陌生,不会把一切都政治意识形态化。
谈到影响力,费博士认为,澳涉华智库对政府在对华外交方面的影响很大,“澳外交部讨论对华政策时就让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的学者参与;议会议员的幕僚也有相关智库学者,比如针对中国‘一带一路’这种新外交战略的分析研判”。有些直接由官方资助的机构,很多人员是从政府机构过去的,比如有学者是情报官员出身。不过,“这种影响能达到何种程度,要根据具体形势和问题定”。
针对被认为“客观中立”的“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费博士表示该智库所在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是拿联邦政府预算运营的,所以其下属的中国研究机构也可以算作政府智库。因为澳政府讲究实用主义,诸如中华全球研究中心这样有政府背景的智库一般不会走极端,不会特别远离中国,也不会特别亲中。中华全球研究中心“务实”的特点,从它邀请休·怀特及其所持观点便可窥一二。
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是澳大利亚为数不多的专门针对中国的研究机构。相比欧美国家,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起步较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澳汉学家费子智的数本著作出版,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成果开始引起世界关注,但整体中国研究还具有一定局限性。转折点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开始偏向亚洲,在此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于1989年在墨尔本大学宣告成立,对中国的研究在澳大利亚逐渐推广开来。
提及澳大利亚存在“反华”的中国智库一说,费博士表示,很难将一个智库用“反华”或者“亲华”来归类。澳大利亚智库中的人员立场分化常常很大,即使在一个智库中,有些学者倾向于对中国持温和态度,有些比较激进,这其实和他们的学科背景和关注点有关。
而对于“一般真正处理过澳大利亚外交事务、在一线有工作经验、受过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训练,以及推动中澳建交和‘脱欧入亚’战略的学者,相对来说会对中国有全面、客观的认识,比如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任格瑞,以及澳中关系研究院的鲍勃·卡尔。”费晟解释说。任格瑞有26年的外交经验,两度在北京任职,当过澳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而另外有一批学者是国际政治专业训练出身,研究国际或地区战略和安全问题。费晟表示,他们基本上完全受美国国际政治训练影响,缺乏对中国历史和内部问题系统的关注,只是出于特定国际政治理论的分析习惯、或者只把中国作为澳大利亚外交的一个当前客体认识的。“这些人对中国的态度和印象容易比较刻板,无论如何要维护澳美关系,对中国所有的积极活动都容易理解为威胁或者挑衅等负面信息。他们对中国本身了解不多,把中国放置到一个他们接受的结构中去研究,很容易把中国往消极方面去理解。”
费博士同时强调,这并不绝对,比如澳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主任布兰登·泰勒是研究地区安全和战略问题出身,但他对中国就十分友善。此外,有一些中国研究学者的配偶是华人,因此他们至少在文化上对中国不那么陌生,不会把一切都政治意识形态化。
谈到影响力,费博士认为,澳涉华智库对政府在对华外交方面的影响很大,“澳外交部讨论对华政策时就让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的学者参与;议会议员的幕僚也有相关智库学者,比如针对中国‘一带一路’这种新外交战略的分析研判”。有些直接由官方资助的机构,很多人员是从政府机构过去的,比如有学者是情报官员出身。不过,“这种影响能达到何种程度,要根据具体形势和问题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