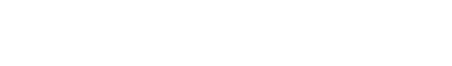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最新动态
我中心费晟副教授就宝林·韩森复兴发表评论——“反全球化”与宝琳?韩森的复兴
发布日期:2016-08-03
2016年08月02日,我中心费晟副教授在《澳洲新快网》发表评论:
议会民主制的特点就是什么样的声音都可能在选举中得到表达,从这个角度看,澳大利亚政坛出现宝琳·韩森这样的极端意见领袖并不奇怪,我们甚至可以秉着“认真你就输了”的态度去对待。然而最近一段时间,本该只是杂音的极端意见甚嚣尘上甚至登堂入室,这就引人深思了。一度被判定为不合法的“单一国家党”以及名声扫地的宝琳·韩森卷土重来并且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这当然标志着澳大利亚政坛的某些新风向: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反全球化”的保守思潮。

对于倍受其攻讦的华人社会而言,除了广泛表达担忧、反感与谴责外,理解其出现的背景或许能更好地帮助大家稳定情绪,进而更理智和理性地与之抗争。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自1970年代白澳政策彻底废弃至今,多元文化社会的价值观已经成为主流政见。但是这也有两个后果,其一是作为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说教并不足以解决现实中不可避免的阶级、族群以及地域发展矛盾问题,它压抑许多本该发生的争论。其二就是近年来的全球化问题不仅给澳大利亚带来许多机会,也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澳大利亚底层民众造成了剥夺感。
从某种意义上讲,包括宝琳·韩森在内的所有澳大利亚人都是移民,绝大部分还是现代全球化的产物。地广人稀的国情意味着澳大利亚格外依赖全球化,尤其是经济依赖外部市场。这不仅造成一种外向型的出口导向贸易,更意味着劳动力也将持续仰仗移民劳工的支撑。
二百年来,澳大利亚社会始终要面临一种新进的移民融入所谓稳定化移民群体的问题。新来的移民出于生存与立足紧迫感,会对老移民社会造成一种搅局般的“鲶鱼效应”,而老移民群体出于维护既得利益与规范的需要,可能对新移民造成一种抵触性的“挤公交车效应”,即担心后来者会抢夺自己的空间从而排斥之。无论是历史上的白澳种族主义,还是18年前宝琳·韩森的现代版种族主义,其实都是将“新移民群体”刻画为“他者”加以抵制,从而宣泄老移民群体的不自信与紧张。无非是根据肤色来划分“自己”与“他者”。
宝琳·韩森最近的叫嚣增加了一种与时俱进的“反全球化”论调。因为自2001年“9·11”事件以及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都处于一种惶恐不安之中。无论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是否真切,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或者国际极端主义的激进暴力都强烈冲击了西方的价值观优越感,因此西方社会内部出现抗拒乃至同样激进的对抗也就不意外。从英国退出欧盟到美国的特朗普竞选总统,其实都折射出西方对丧失全球化主导权的担忧。更重要的是,这种担忧导致了西方社会传统凝聚力的消失。对此,澳洲许多政客都对社会内部出现的分化问题提出了收紧闸门的对策,韩森只是最极端的之一。
问题在于,几百年来全球化可能有轻重缓急之分,但从来都没有停止,同时没有哪个社会只享受全球化的好处而不面对其冲击。因此,寻找到一条开放制度下保持社会均衡的道路,才是成熟现代国家面对挑战时应有的目标。
如此看来,宝琳·韩森的出现不是坏事,她可以以负面案例的形式提高澳大利亚社会的警觉。
转载自:澳洲新快网微信文章,公众号kingoldmedia01
议会民主制的特点就是什么样的声音都可能在选举中得到表达,从这个角度看,澳大利亚政坛出现宝琳·韩森这样的极端意见领袖并不奇怪,我们甚至可以秉着“认真你就输了”的态度去对待。然而最近一段时间,本该只是杂音的极端意见甚嚣尘上甚至登堂入室,这就引人深思了。一度被判定为不合法的“单一国家党”以及名声扫地的宝琳·韩森卷土重来并且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这当然标志着澳大利亚政坛的某些新风向: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反全球化”的保守思潮。

对于倍受其攻讦的华人社会而言,除了广泛表达担忧、反感与谴责外,理解其出现的背景或许能更好地帮助大家稳定情绪,进而更理智和理性地与之抗争。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自1970年代白澳政策彻底废弃至今,多元文化社会的价值观已经成为主流政见。但是这也有两个后果,其一是作为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说教并不足以解决现实中不可避免的阶级、族群以及地域发展矛盾问题,它压抑许多本该发生的争论。其二就是近年来的全球化问题不仅给澳大利亚带来许多机会,也造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澳大利亚底层民众造成了剥夺感。
从某种意义上讲,包括宝琳·韩森在内的所有澳大利亚人都是移民,绝大部分还是现代全球化的产物。地广人稀的国情意味着澳大利亚格外依赖全球化,尤其是经济依赖外部市场。这不仅造成一种外向型的出口导向贸易,更意味着劳动力也将持续仰仗移民劳工的支撑。
二百年来,澳大利亚社会始终要面临一种新进的移民融入所谓稳定化移民群体的问题。新来的移民出于生存与立足紧迫感,会对老移民社会造成一种搅局般的“鲶鱼效应”,而老移民群体出于维护既得利益与规范的需要,可能对新移民造成一种抵触性的“挤公交车效应”,即担心后来者会抢夺自己的空间从而排斥之。无论是历史上的白澳种族主义,还是18年前宝琳·韩森的现代版种族主义,其实都是将“新移民群体”刻画为“他者”加以抵制,从而宣泄老移民群体的不自信与紧张。无非是根据肤色来划分“自己”与“他者”。
宝琳·韩森最近的叫嚣增加了一种与时俱进的“反全球化”论调。因为自2001年“9·11”事件以及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都处于一种惶恐不安之中。无论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是否真切,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或者国际极端主义的激进暴力都强烈冲击了西方的价值观优越感,因此西方社会内部出现抗拒乃至同样激进的对抗也就不意外。从英国退出欧盟到美国的特朗普竞选总统,其实都折射出西方对丧失全球化主导权的担忧。更重要的是,这种担忧导致了西方社会传统凝聚力的消失。对此,澳洲许多政客都对社会内部出现的分化问题提出了收紧闸门的对策,韩森只是最极端的之一。
问题在于,几百年来全球化可能有轻重缓急之分,但从来都没有停止,同时没有哪个社会只享受全球化的好处而不面对其冲击。因此,寻找到一条开放制度下保持社会均衡的道路,才是成熟现代国家面对挑战时应有的目标。
如此看来,宝琳·韩森的出现不是坏事,她可以以负面案例的形式提高澳大利亚社会的警觉。
转载自:澳洲新快网微信文章,公众号kingoldmedia01